“中国之人,下愚而上诈。”陈寅恪先生这一论断,在历史的长河中已经不断得到了验证。而在今天的校园围墙之内,相似的剧本正在上演,只不过,角色换成了校园权力与普通的教师。
校园本应该是自由思想的绿洲,求知探索的圣地。然而,在教育行政权力日益膨胀的今天,许多学校却成了微型“王国”,教师则在各种精妙的驯化技术中,逐渐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勇气。
校园权力对教师的驯化,首先是从信息控制开始,他们通过信息控制,制造“清醒的盲人”。
选择性信息流动已成为管理常态。普通教师如同“需要知道原则”下的士兵,只能接受经过筛选的信息。学校发展的真实方向、资源分配的实际标准以及学校决策背后的真正考量,这些关键信息往往被锁在校园权力的圈子之内。
更精致的则是信息过载战术。各种会议、表格、汇报、总结,以铺天盖地之势向教师涌来,让教师在信息的海洋中溺毙,无暇思考真正重要的问题,教师们都在忙于填写各种表格,证明他们在工作,却没有时间真正工作。
而评价体系的不透明则是信息控制的集大成者。职称评定、优秀选拔、绩效分配,规则模糊而且变动不定,使教师永远处于不确定状态,只能仰仗权力的恩赐。
在有些学校里,教师们直到学期末才得知评价标准已经悄悄改变了;在有些学校里,教师绩效考核的算法复杂到无人能解,结果却要求教师必须全盘接受。信息控制的高明之处在于,它让教师们睁着眼睛却看不见真相,成了“清醒的盲人”。
校园权力的第二大驯化工具,是逻辑的系统性扭曲,让教师把奉献变成自我牺牲。
无私奉献的道德绑架是最常见的手法。“一切为了学生”、“为了学生的一切”、“教师的崇高在于奉献”,这些冠冕堂皇的口号,掩盖了校园权力对教师的剥削。超时工作成为了美德,教师争取权益反倒成了“缺乏师德”的表现。
有些学校要求教师每天提前一小时到校值班,却不计任何报酬;有些学校总是占用教师休息时间,选在大中午或者晚上开会,教师质疑却被斥责为“缺乏教育情怀”。在这种扭曲的逻辑下,教师的自我价值感与自我牺牲程度挂钩,最终从被迫服从转变为主动奉献。
教师竞争个人化又是另一大高明的逻辑陷阱。当学校资源有限时,权力不是寻求公平分配,而是迫使教师相互竞争。如教师职称名额、优秀指标、教学奖项,都成了稀缺资源,教师们都只能在零和游戏中内耗。
教师们不再是同盟,而是竞争对手。他们不会联合起来争取权益,而是各自盘算如何打败同事而获得晋升。在这种逻辑下,教师间的团结土崩瓦解,每个人都成了孤岛。
最精妙的则是去专业化的操控。通过繁琐的检查、格式化的教案要求、僵化的教学评估,校园权力实际上否定了教师的专业自主权。教师不再是教育专业人士,而是执行命令的技术员。
语言是思维的边界,当语言被污染,思考也随之扭曲。教育行话的泛滥制造了一种虚假的专业主义。如“翻转课堂”、“智慧教育”、“核心素养”、“深度学习”,这些不断更迭的术语,常常是旧酒装新瓶,却迫使教师不断追赶“时尚”,无暇反思教育的本质。
更隐蔽的则是批判语言的污名化。当教师们提出不同意见时,往往就会被贴上“负能量”、“不团结”等等标签。
而感恩话语的强制使用则彻底扭曲了权力关系。“感谢学校提供平台”、“感谢领导栽培关心”,这些表达不再是真诚的情感流露,而是必须表演的忠诚测试。
最可怕的控制,是让人自己成为自己的狱卒,监视已经内化成为了本能。
在校园中,各种评价与监控机制已经使得教师时刻处于被观看状态。随堂听课、推门听课、教案检查、学生评教、绩效排名,这些监控手段使教师开始自觉按照权力期望的方式行事。
有教师坦言:“我现在备课,首先考虑的是如果有人听课,我会被如何评价,而不是学生真正需要什么。”
集体备课、教研活动这些原本旨在促进专业交流的平台,也常常异化为思想统一的工具。在这些场合,异议的声音会被无形地压制,共识被强制达成,不同的教育理念被悄然地消音。
而教师职称晋升的诱惑则是最终的驯化工具。为了那一纸聘书,许多教师学会了揣摩上意,放弃原则,最终成为体制的共谋者。
然而,教育终究不能等同于驯服。当教师们成为了被驯化的群体,教育也就失去了灵魂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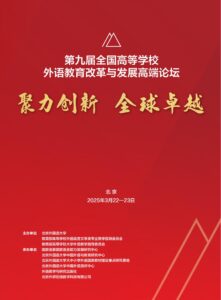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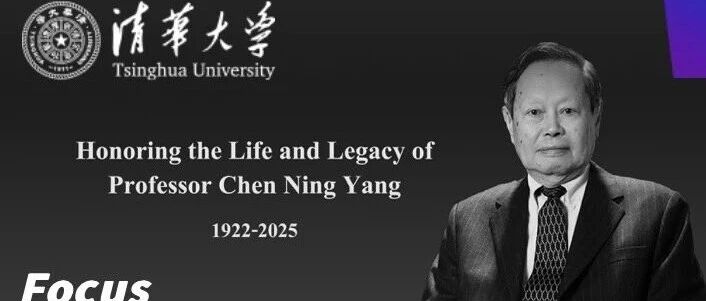




暂无评论内容